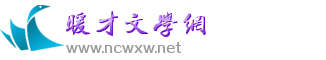康熙正要叫过熊赐履来议关羽赐号,猛听台上箫鸣筝响。《桃花扇》第一出《听稗》开场了,侯方域方巾皂靴甩着水袖出来,一开腔便吸引了康熙:
孙楚楼边,莫愁湖上,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,酒卖斜阳,勾引游人醉赏,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,那些莺颠燕狂……
康熙静静地望着台上,倏然间想起伍次友,正是侯朝宗的高足,前次派素伦至五台山,回说他挂单化缘去了,如今在哪里呢?他的心不由一阵凄凉。因思自己年过而立,台湾战事凶吉未卜,西部叛乱无暇顾及,既无良将可当巨任,又无向导随行参赞,不自禁叹息一声。又看了一会儿,见天色已近申时,便起身进大厅来。一大群嫔妃命妇正立在太皇太后跟前凑趣儿,见康熙进来,“唿”的一声都跪了下去。
太皇太后正扯着芳兰的手说家常,见康熙进来,笑道:“外头大臣那么多,皇帝进来做什么?我老天拔地的,这些戏文都听不懂,有她们陪着说笑解闷儿罢了,不要你来立规矩。”康熙赔笑说道:“坐得久了也想走动走动,天这早晚了,又怕老佛爷饿了,进来瞧瞧,可要传膳?”太皇太后道:“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,还饿着我老婆子了?只芳兰可怜见的:一个新媳妇,踏进门就应付这么大的场面,真难为她了。”
芳兰听太皇太后提到自己,忙闪出来向康熙叩头。康熙见她还穿着大红喜服,越发显得面白如月,羞颜似晕,俏丽中透着精明,遂笑道:“好好!起来吧。朕原说过为高士奇主婚来着,总算不食前言了。这会子没东西赏你,回头让礼部早些给你进诰命!”太皇太后因笑道:“你没事还去吧!没的在这里,她们连个笑话也不敢说,你饿了只管传膳,我是不用的。”
康熙出来,戏已演到中部,弘光帝败亡之余偏安一隅,不思振作,却一门心思搜求美色,又不肯直说,叫马士诚“猜”他的心思。老奸巨猾的马士诚却故意屡猜不中。康熙不禁一皱眉,大声说道:“伪君子!”
明珠怀着鬼胎,哪里有心思看戏?一会儿看看高士奇,一会儿偷看康熙神色,猛听康熙这一声,吓得身上一抖,好一阵才想起康熙是说马士诚。
至《选优》一场,弘光和诸歌女打十番取乐儿。弘光帝一手举扁鼓,一手打莲花落,蝴蝶穿花似的在十几个歌伎中穿行,这儿丢个眼色,那儿送个秋波,生角做工极到佳处,捏着嗓子唱道:
旧吴宫重开馆娃,新扬州初教瘦马。淮阳鼓昆山弦索,无锡口姑苏娇娃。一件件闹春风,吹暖响,斗晴烟,飘冷袖,宫女如麻。红楼翠殿,景美天佳。都奉俺无愁天子,语笑喧哗。
康熙看得兴起,不禁失声大笑,回身对熊赐履道:“像这样全无心肝的人居然也做了天子!弘光弘光,虽欲不亡,其可得乎?”
“万岁说的极是!”从不看戏的熊赐履也入了神,见康熙和自己说话,忙笑道,“天夺其魄,以神器授我大清!这戏虽是稗史,却也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呢!”
纱幕后陪着太皇太后的苏麻喇姑却又是一种感慨。侯公子和李香君在明亡之后相继出家,数十年弹指一挥,他的学生竟和他一模一样的落局。情事虽异,心境相通,心中一阵酸热几乎坠下泪来。太皇太后见她面色苍白,知道戏文勾起了她的心思,一笑说道:“戏文虽好,只是太文了,我有点坐不住。天色渐渐暗下来,趁他们掌灯,咱们不如回宫。你也不用回畅春园,陪我住一宿吧……”说着便起身,吩咐张万强道,“你陪着皇帝看戏,让他歇息一日,别说我去了,扫了皇帝的兴。”又拉了芳兰的手说道,“没事进宫陪我说说古记儿解闷。”说完,便从后门命驾回宫了。
戏一直演到子初时分才完,康熙看得快心畅意,赏了戏子们,又命众人散了,兀自兴致勃勃地索茶,笑着对高士奇道:“实在是才子手笔,这么好的戏,为什么不早奏朕?”高士奇笑道:“孔尚任这人是有名的大胆秀才,虎臣怕里头有什么违碍之处,先在南京演了才进上来,奴才原也想先看过了再请主子赏看。后来想虎臣何等精细人,岂能有错?就斗胆了。”康熙笑道:“孔尚任是伍先生荐过的人,即有小过,有什么干系,用得着你绕那么大圈子请朕?只不知北闱科考孔某来了不曾,别再像南闱一样黜落了吧?”
高士奇耗精神,为的就是南闱的事,好容易总算说到题目上,忙道:“主子说到这儿,奴才就得进一谏,前儿万岁盛怒,天威不测,奴才被吓得走了真魂,就有话也得等主子消停消停再说——若论南闱的事,只能说臣工办事不尽忠心。要是翻过来瞧,还是件喜事,值得万岁龙心大怒,动那么大肝火?”
“你说什么?”康熙问道,“科场舞弊,有什么可喜之处?”
“万岁,万事都得反过来看看,才看全了!以奴才之见,此乃天下文人心向大清,盛世即来的转捩!”
“唔?”
“我朝定鼎已四十载,人心浮动原由很多。”高士奇款款下词,“最大的事莫过于文人执拗,谬解圣人经义,死抱了华夷之见。所以历届科考皆都不足员。”
“嗯……”
“如今人们不惜重金钻营门路入仕,乃政局大稳、百废俱兴之象。”高士奇执壶给康熙添了水,继续说道:“奴才说句不中听话,开国之初时连明珠那样的诗还中个同进士!‘三藩’乱时,南闱报考不足五分之一,也不敢停考,那时怎么没人花钱打关节?时事不一样,大势有变了!当然,有舞弊必有屈才的事,毕竟还是少数。奴才看了中选名单,南闱取中的江南名士也不少,似也不可一概抹杀……”
康熙站起身子,端着杯子来回踱起来,见高士奇嗫嚅着停了口,笑了笑道:“你说下去,不要怕嘛。”
“万岁认真要办,就得兴大狱。”高士奇眉棱骨挑起老高,忧心忡忡说道:“真的像熊东园说的,主考、副主考,一十八房考官杀的杀、砍的砍,这取中了的文士谁不胆战心惊?办得如此之严,往后的考官也要望而生畏!多少年才养了这点文人归心的风气,岂不又扑灭了?而且南闱闹事主犯邬思道并没有拿住,背后有什么文章也不清楚,严惩考官必放纵了这些人,往后动不动就抬财神进贡院,万岁办是不办?这善后何其难也!”
康熙思索着,将茶杯向桌上一蹾,似笑不笑地说道:“你八成受了什么人托付,趁着朕高兴,平息这天字第一号官司的吧?依你说的,贪赃坏法,徇私舞弊,竟作罢不成?”
高士奇吃了一惊,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下,说道:“奴才岂敢!奴才原是潦倒书生,跟了主子,不次超迁,已经贵在机枢,焉敢以身试法?奴才是说,舞弊当然不好,但主上乾纲在握,这毛病好矫治;动了人心不易挽回。主上天聪睿智有日月之明,自能洞鉴奴才苦心!”
本来决心大开杀戒的康熙被高士奇的如簧之舌深深打动。想想,又觉确有他的道理。但撒手不治,又于心不甘,默谋良久,康熙方喃喃说道:“不办了?”
“办还是要办,明面儿上不能声势太大,惊动朝局!”高士奇吃准了康熙急于用兵不愿朝局震动的心思,断然说道,“将左某、赵某调回京师,严加申斥,夺官退赃!闹事者颁密令查拿。待台湾事了,主上南巡,落卷中确有才识的简拔上来。这样,已选上的贡士不致玉石俱焚,落第才士又得特简之恩。将来察看他们的吏治,公忠廉能的擢升,贪墨不法者治罪,岂不是更好?”
康熙听到此,不禁双掌一合,刚要说“就依你”,话到唇边却变成了:“朕今儿乏了,明日召见上书房和礼部司官合议一下再说吧!”
回至大内,已是子末时分,康熙便没再翻牌子,径住了养心殿。这夜的戏使他浮想联翩,难以入睡,便索性披衣起来。三年来,每隔半月康熙都要亲自观星,从不间断。今天虽不到日子,但既然睡不着,何不观星呢?太监李德全还在廊下熬鹰,见康熙出来,忙过来请安,要叫值夜太监过来侍候。康熙摆手说道:“朕想独自静一静儿,围一大群人叫人心烦——海东青这几天吃的还好?”
“喳!”李德全打千儿起身,回道:“——海东青壮着呢!吃的也好,只不过也得放放,它急得什么似的,见人就又咬又叫。没奴才在跟前,一口东西也不肯吃……”
康熙没再理会,下了丹墀,在寂静的天井里散步。中天冰冷的残月,恰如一把玉钩,若明若暗,将宫墙顶、殿角、呆罳、铜马镀上了一层银光,一切都笼罩在影影绰绰、恍恍惚惚,似真似假、似有似无的霭气之中。
“多快啊!”康熙倚着琉璃照壁,仰脸望着满天繁星,不由深深吁了一口气。二十二年前他是从这天井乘龙舆至乾清宫柩前即位、君临天下的,当时是什么心情,如今已是模模糊糊。但十年前腊月在这里发生的一幕幕情景,他到死也忘不掉。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派的刺客皇甫保柱,就是从西边房顶上跳下来,当场向自己投诚的。杨起隆腊月二十三造反,这里一片骚乱,穆子煦和武丹连诛十几名太监才镇住逆党气焰……这几年是没了这些事,但朝廷的大事似乎比前更繁更重,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索额图、明珠这两个奴才,康熙八年前好得像穿一条裤子都嫌肥,如今却明争暗斗,愈演愈烈——康熙倒并不担心他们龃龉,亲信大臣之间应该有点距离,但闹得如此水火不容,也是不成体统的!
康熙拍了拍冰冷的铜鹤,又踱了几步,心里仍不住翻个儿:索额图是皇太子的外叔祖,事事护着太子自是情理中事。但明珠极伶俐的一个人,怎么反倒与太子为难?太子穿了件异样的衣服,就唆使言官弹劾?才十岁的娃娃,有什么碍着他的去处?明珠不晓得,储君早晚有一日要做皇帝,不怕灭他的门么?康熙目光炯炯,反复猜着这个谜儿。
“失恃儿!”康熙眼波一闪,想起幼时乳母孙嬷嬷讲的“没娘孩儿”故事,有了后娘就有后爹:“一定是打这个主意。太子无母,宫中无人保护,朕又当盛年,将来不免有宠母夺嫡之事!”康熙望了望后宫,冷冰冰一笑,又向前踱去。
这时已是丑末时分,天际西北一片藏蓝色的夜空,出现了一长条模糊的光。白白的,像谁用笔蘸了水银轻轻抹了一道。它的出现,立刻吸引了康熙全部注意力。他揉了揉眼,觉得还是不甚分明,便快步回殿,从大金柜顶取出一个万花筒模样的东西——这是西洋人张诚从欧罗巴进贡的一件玩意儿,叫“望远镜”。为此,康熙恩准在苏杭一带建了三座天主教堂,一座东正教堂。当下康熙调了焦距,对着一看,不禁失声叫道:“彗星!”
是彗星,它刚刚出现,正用难以觉察的速度向紫微座东南移动。渐渐地,不用望远镜也瞧得很清楚了。
“离帝星如此之近!”康熙心中一沉,厉声喝道:“来人!”
“喳!”李德全带了四个值夜太监应声而至。
“传钦天监正!”
彗星出现很快就引起朝野的严重关切。但康熙却没有立即下旨令群臣议论。直到第五日朝会,方令各部院大臣各述己见。这日五鼓时分上书房大臣便乘轿直趋乾清门。各部尚书、侍郎以上足有六七十人,有的鹄立檐前,有的交头接耳,有的在天街向西北遥望,等候着,一边思量如何应对康熙的问话。明珠原料康熙一定提前命递牌子请见的,谁知等了半晌也没个音信,叫过乾清宫太监问时,才知康熙斋戒五日,今儿一早便去天坛拜祭,回来即奉太皇太后懿旨,逼着小酣一个时辰才许见外臣。直到辰初时牌,方见康熙的乘舆抬进天街。熊赐履等长跪在地,默默恭侍他进了乾清门。
“彗星的事大家都晓得了。”康熙坐定,等众臣依次鱼贯而入,行过礼,便开门见山地说道,“这种事史不胜书,算不得什么稀奇,只是眼下出得不是时候,也不是地方,因此召你们来议议。”他从容喝了一口刚进上来的鲜奶汁,又道,“太皇太后方才说的很有道理,有天变要想人事,但这天变连的什么人事得仔细斟酌——有什么讲什么,不必忌讳。”
明珠因南闱的事余惊未消,生恐有人借题发挥,双膝向前微挪半步,率先说道:“臣以为历来彗星出现,多应国家用兵之事。彗星出于西北,移向帝星,正应准葛尔部侵入漠南蒙古,黑龙江地域又有罗刹国将领莫里尼克率哥萨克掠夺我木城、雅克萨城,所以天象示警,求圣上明鉴!”
“黑龙江和准葛尔之事已非一日,且黑龙江在东北。”索额图忧郁地说着,“主上前已诏命巴海、周培公相机痛剿,颇见成效——这天变何以仍旧出现,臣实愚鲁,不明其理。”索额图为江南秋闱的事窝了一肚皮的火。他因康熙主张严办,已着吏部下文霹雷火闪地革掉了几个地方官的顶戴,但朝旨一颁,“正凶”主考、副主考只是革职回籍,各房房官也不过罚俸铸级,一场轰轰烈烈的泼天大案,又被莫名其妙地“阴干”,索额图倒落了刻薄寡恩的名声。索额图见康熙沉吟不语,正要再奏,李光地在旁朗声说道:“臣以为西北东北都不相干。乃朝中小人作祟、紊乱国政、坏国家抡才大典、贪财枉法欺蒙主上。因此彗星出在紫微之侧!”
这话说得十分慷慨,部院大臣无不悚然动容。康熙略一思索,一倾身子问道:“李光地指的是谁,不妨明言。”李光地一怔,心知必是明珠,却没有证据。良久才说道:“臣不知内情,不能实指。但罪重罚轻有目共睹。求主上圣心默察,不难寻出小人,小人一去,彗星自消!”
高士奇向来一帆风顺,还是头一遭遇到这样直接威胁自身安全的事,看着索额图不阴不阳的面孔,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但此时贸然出奏,无异于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,帮索额图查明了谁是“小人”,便自拿定了主意:只要不点老子的名,就当你说的是旁人。心里一静,脸色也就泰然,只呆呆望着康熙出神。熊赐履不知内中委曲,不敢妄言;明珠知道一开口,必遭更多人攻讦,也自缄口不言。上书房臣子不开口,部院大臣谁肯出这风头?一时间殿上空气仿佛凝固了、板结了,死一样寂静。
康熙不动声色地喝着奶,瞟一眼大臣,正与户部尚书梁清标四目相对,便笑道:“今日言者无罪。梁清标,你像是有话要讲?”
“是!”梁清标清了清嗓子,亢声说道:“既然上天示警,必是最大的事,何谓朝廷今日最大之事?”他自设一问,接着又道,“自然是台湾!记得‘三藩’之乱粗定,我皇曾下明诏说,今大逆削平、疮痍未复,罢兵、养民,与天下休息——臣当时聆旨,不觉欢欣鼓舞,感激涕零,以为天下承平有日。不料圣谕明发不及二载,不知何故皇上又改初衷?夫台湾乃化外一隅之地,顽寇盘踞,隔海相争,实劳民伤财之举!兵凶战危、胜负不测,所谓‘罢兵养民’何在?又闻皇上尚在筹划西部战事,如此看来,连年兴军兵,所谓‘与天下休息’岂非空话?”
这位梁清标一开口便是一记杀手锏。他在撤“三藩”之初,曾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尚之信处传旨,九死一生逃回北京,人人目为忠贞之士,所以说话毫无顾忌,连康熙的脸色也不看,只顾唾沫四溅地侃侃陈词:“上天垂警,臣以为指的就是皇上自食其言。若能改弦更张,撤施琅水师屯田养息,罢西征之计划,则彗星必悄然而逝……”
康熙听他大放厥词,说自己食言,脸都气白了。想想自己曾说过“言者无罪”,忍了几次才算听完他的高论,冷冷问道:“说完了?还有没有呢?”
梁清标已听出康熙口风不对,连连叩头道:“容臣奏完——臣以为福建将军赖塔所奏,乃是老成谋国之言——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、徐福之日本,与世无患,与人无争,而沿海生灵永无涂炭之虞!”
“台湾自汉已入中国版图,宋时已为晋江县治辖区。梁清标,你和赖塔一样,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!”康熙狠狠盯着梁清标,只是为了“言者无罪”的诺言,才按捺着没有咆哮起来,“朕是说过‘与民休息’的话,但如今国土不全,金瓯有缺,海域有顽寇割据,四塞有不安之民,敢问你梁清标,叫朕如何‘休息’?”他虽然没有拍案大怒,震怒之情溢于言表,句句说得掷地有声。梁清标垂了头,正思量如何回话,身后的李光地朗声奏道:“臣以为主上所言乃是堂堂正理,梁清标不知天理,昧于人道,实属昏聩!上天垂象西北,彗星向帝星东南移动,正应天兵克日扫荡海域——应即下诏,令施琅麾军渡海,犁庭扫穴,可以毕其功于一役!”
李光地是举朝第一个上书请兵进击台湾的,因为赞成者少,他受了多少日子的窝囊气,便乘着康熙严斥梁清标时,挺身出来加了一句。梁清标本已无言可对,李光地用话一激,又上了拗性,叩头道:“李光地固然知天理、通人道,却不晓得用兵易,筹粮难!臣以为即便要取台湾,也应等漕运畅通、兵粮调遣应付裕如之时。须知一战失利,东南遗患无穷——求主上明鉴!”
“这个话尚在情理之中。”康熙蹙额叹息一声,说道,“台湾之事,听听施琅和姚启圣怎么说,再作定夺吧。”说罢立起身来,徐徐下了龙座,在一大片跪着的臣子中踱着方步,提高了嗓音说道:“君子畏天命是圣贤之言,但天变之理定要格外慎重。康熙八年彗星出,有人说于朕不利,朕恰在那年除了鳌拜;十年地震,京师谣言蜂起,朕镇之以静,安然无事;十二年冬彗星再现,吴三桂谋反,朕决意撤藩——结果如何?你们都看见了!朕劝你们一句话,要做贤臣、能臣,不要做忠臣、烈臣。有贤臣,便有明君,有能臣,则有治世;出了忠臣,便是君昏国乱之时。诸臣工清夜扪心自问,尔等所言所行,是为朕、为民、为社稷想的多,还是为你们自家沽名钓誉、树帮立党想的多?——散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