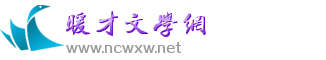武丹原是关东马贼出身,生性最是粗野,一开口便伤人,穆子煦慌忙上前制止。他打量了一眼这个测试风力的汉子,笑问道:“大哥,既然这里不能呆,你为什么在这里呢?”
“我是河伯陈天一!”陈潢冷冷说道,“这位出口伤人的有种,就让他留在这里,你们快走吧!”他一边说,手比目视一刻不停,看也不看康熙一行,又道,“桃花汛一个时辰就到,这里顷刻间就是一片汪洋!”
康熙听见这话,反而下了马,过来问道:“你的命不是命?我舍命陪君子!”熊赐履顿时急了,不管这人是疯是傻,桃花汛在这季节肯定是有的。他深悔今日粗心没有虑及,忙上前一把扯住康熙,说道:“龙爷,没什么好瞧的,且到镇里打尖儿去——这位兄弟,多谢提醒了!”康熙一边跟着走,一边大声道:“既这么险,你也快走吧!”
“我要测水量水位,此刻千金难买。”陈潢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声,又颇自得地扬言,“淹死我的水下一辈子才能来!”说着,便急步向上游走去。
康熙君臣十余骑一阵疾驰奔回铁牛镇,在镇边一个过路干店棚下坐了。康熙要了一盘黄河鲤鱼,一桌小菜,一边吃,一边心神不定地翘首望着河边,夹了几次菜,都从筷子上滑了下去。这里距黄河有七八里远。众人见镇上人来来往往,熙熙攘攘,一切都很平静,也就放了心。穆子煦见康熙心神不定,因笑道:“林子大了,什么鸟儿全有——也不知那人是个疯子,还是个痴子,主子别理会他!”康熙听了略一点头,坐了默默吃酒。熊赐履和杰书一边坐一个,不敢动箸,只拣菱角、鲜藕小心地品着相陪。
过了好一阵,陈潢也从河滩上走过来,向店主买了两个烧饼、一盘牛肉干,老实不客气地坐在康熙对面,手撕口咬大吃大嚼。康熙悄悄取表看了,已近一个时辰,揶揄地笑道:“我说河伯老兄,你怎么放了一个哑炮呢?方才不是你说一个时辰大水即到么?”
陈潢没有立即答话,瞧瞧棚柱日影儿,又向上游望望,将一大片牛肉塞进嘴里,含糊不清地说道:“再好的表也没日头准——少时再看!”杰书和熊赐履见他兀自吹牛,不禁失声而笑。武丹怪笑着对穆子煦道:“你我兄弟也算见过点世面的了,可从未见过这么一位吹死牛不倒架的活宝呢。”
但他们的脸色立刻就变了。因为沉雷一样的河涛滚动声已隐隐传来,大地都被撼得簌簌发抖。宁静的铁牛镇顿时哗然大乱,地保满头大汗,筛着锣飞也似的跑着大叫:“潮神爷来了!居民人等,都到东岗上回避了——”人叫声、狗吠声,老太太念佛声、孩子的哭叫声,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……搅得开锅稀粥似的,一群群人连成片、滚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。
“爷们,发哪门子呆呀!”店老板脸色煞白,慌慌张张跑过来,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,旁边几个人也都僵立着,急急地说道:“今年不比往年,河堤全垮了!快,快走!”
“这真是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”陈潢只起身望望,反而又坐了下来,破颜一笑说道:“此乃铁牛镇,有神牛镇水,何惧之有?你们走吧,这么好一桌酒菜,只便宜了我陈某。明日回邯郸,正好为我北上饯行!”康熙已知陈潢的能耐,一把扯住陈潢道:“明日我为你摆酒,在这里太险了!”
陈潢看了看康熙,摇头道:“多承厚爱,我须要留在这里看潮。放心吧,桃花汛来不了铁牛镇!”康熙见素伦和德楞泰扑过来要扶掖自己,一摆手制止了,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:“为什么?你是神仙么?”陈潢一怔,随即大笑道:“哪里有什么神仙!我告诉你,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,铁牛镇一带河宽五百丈,均深七尺,加上洪水,不过上涨两丈。河岸距镇一千一百丈,这沙滩便是天然屏障。水上沙滩,流势缓冲,泥沙必淤,愈积愈高,说不定淤起一条长堤来。这可节省皇上几十万银子呢……”他说得滔滔不绝,把个康熙听得愣了神。陈潢一边指手画脚,一边夹起牛肉往嘴里送,还要长篇大论地说,早被武丹照脸啐了一口:“闭住你的狗嘴!你八成是个疯子,活腻了!在这里等着喂王八吧!”熊赐履大喝一声:“德楞泰、素伦,架着主子快走!”
德楞泰和素伦“喳”地答应一声,不由分说将康熙扶到马上,武丹向马屁股狠命就是一鞭,那马狂嘶一声扬尘而去。武丹阴沉着脸上了马,鞭杆儿指着陈潢的鼻子恶狠狠说道:“你这王八蛋,活着出来,可别撞到老子手上!”说罢“笃”的一声打马而去。偌大镇子立时空落落的,只有一个陈潢在棚下稳坐。此时河涛的呼啸声已如千军万马般铺天盖地而来……
但黄河水毕竟未进铁牛镇,头汛过后,竟果真奇迹般涌出了一道丈余高的天然沙堤。第二日凌晨,康熙派穆子煦飞马到镇上来看,逃水的人们尚未回镇,只康熙一席丰馔被陈潢吃得杯盘狼藉,人却不知哪里去了。
回京路上康熙为此一直不悦。小太监秦哲不知他的心事,变着法儿逗乐儿讨他欢喜,竟惹翻了康熙,令人扒掉他的裤子打了个臭死。武丹虽心粗,却也知是自己误了康熙的事,见他拿人作法出气,一路更加了小心,生怕触了霉头,连道貌岸然的熊赐履也变得有点蹑手蹑脚的了。
安徽巡抚靳辅因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,办事向来迅速。奉旨后,两个月间,便将手中积案清理了,并将未了的文案俱一应移咨藩司衙门代理,又命两个师爷先至清江查看黄、淮、运三河交叉处,准备提奏将河督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。一切预备停当,便叫了他最得用的幕宾封志仁过来下棋。其实,他哪来的闲心,他正为即将上任的河督发愁呢!
靳辅自幼酷爱水利。康熙十年他受任安徽巡抚,恰逢黄河改道,贯境而过。他初试治水之道,居然颇见成效。但是要接任治河总督,靳辅心里却很有点忐忑不安。黄河从三门峡向东,水势平缓,至徽宁一带由于地形更加平坦,泥沙沉积,将河床愈淤愈高,远远望去,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,因而名叫“悬河”。历来地方官对河督一职视为畏途。如今朝旨虽未下,明珠来信已透出了出任河督的信儿,靳辅虽说由正二品晋为从一品,反倒显得有些神魂不定。
对面坐的封志仁见他走神儿,晓得他有心事,两手“咔咔”地敲着吃下的棋子儿不言语,翻着眼不时地看看靳辅。他知道靳辅脾性,自己就是不问,这位东翁迟早也会自己说出来。
“现在的事还成个什么体统?”果然过了一会儿,靳辅舒展了一下眉头,自言自语地说道,“这外官愈来愈难做啊——手长些要钱,老百姓骂你是民贼;不要钱,打发不了上司,朝里就有人诬你是国贼……反正进退都是个贼名儿!唉……”
封志仁点了点头,走了一着“高吊马”,问道:“东翁,这次进京,带多少钱?”
“唔?”
“我是说,带少了是不济事的。”
“带了一万五。”靳辅微笑道,“这回我也要做贪官了。河工银子下来,这笔账要开销出去。河督不比巡抚,这个坑我填不起。”“一万五!”封志仁轻声重复一句,狡黠地眨了一下眼,说不清是个什么神气。靳辅看了他一眼,诧异地问道:“怎么,不够使么?”
封志仁搓搓手,若无其事地一笑,说道:“够使不够使哪里说得清!中丞只要有人缘儿,一个子儿不花也是有的。封疆大吏是什么行情,我真的不晓得。我的同乡刘瞎子捐了个同知,捐银只三百两,投的是明相门路,门包一千七、堂官五千,实到明相手里八千,才放了个实缺知府。江西刘汝本,用一千五百两金子打了个佛爷送索中堂做寿礼,票拟下来即授淮西盐道。还有我的一个表亲徐球壬,月头里进京,听说带了五万……这和做生意竟是一个理儿,买者情愿,卖者甘心,一分价钱一分货,言无二价,童叟无欺!”他说着,靳辅已是脸上变色,身子一仰,梗着脖子道:“要是这样儿,我一个也没有!我做到这么大官,不能那么下作。这一万五也不过买个平安,要是还不行,只好随他便!”
正说到此,门上司阍走进来禀道:“中丞,外头有个年轻妇女,带着两个孩子,想求见中丞——说是李安溪大人的家眷……”说罢,嘴唇嚅动了一下,欲言又止。靳辅听了一愣:李安溪就是李光地,平素只有见面情分儿,如今他是国家勋臣,怎么会将妻儿托付给自己,又怎么会连封书简、名刺一概没有,母子三人就上门来拜?心下正疑惑着,口里却吩咐道:“你站着愣什么,快请进来!”长随躬身答应一声:“是……不过他们三个人……奴才瞧着实在不像官亲。那衣裳破得像叫花子似的,鞋子都绽了……”
靳辅听得站起身来,又一屁股坐了回去,有点不知所措地瞧瞧封志仁。封志仁问道:“你没有告诉她,靳大人没带家眷,不便接待,而且即日就要离任进京?”长随忙道:“回封爷话,奴才说了。她说正是听说中丞进京,请中丞念同朝为官情分,带她母子同行,投奔李大人,她身上是一文盘缠没有了……”靳辅略一踌躇,叹了口气说道:“既如此,请进来见过再说吧。”
片刻,果见长随带着一个衣饰褴褛的年轻妇人进来。靳辅看时,她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,细挑身材,瓜子儿脸上细细两道八字眉,眉尖微颦,虽是神色憔悴,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显得很有精神,一手拉着一个孩子踽踽地进来,不等靳辅说话,先蹲了两个万福,便跪了下去,轻声说道:“贱妾李秀芝叩见靳老爷……”靳辅用手遥遥虚扶了一下,说道:“尊夫人请起,看座,这断不敢当,晋卿大人乃当今天子幸臣,靳辅倚重正多,这如何使得?”
“回大人的话,”李秀芝坐了,接过下人递上来的茶,红着脸说道,“这是礼所当然,贱妾不是晋卿的正配……”说着将茶递给左手的孩子,颤声说道,“兴邦,你喝点,再给弟弟……”那孩子端过茶只喝了小半口便递给右首的孩子,道:“兴国,你喝……”兴国大概渴极了,接过来便喝了个底朝天。
封志仁留心看时,这两兄弟一般个头,一般装束,一般相貌,大约七八岁的模样,极似孪生兄弟,因问道:“在下封志仁。恕无礼,不敢动问李太太何以沦落至此?”秀芝眼圈一红,欠身说道:“我们母子三个变卖家财,从杭州到福建安溪,投亲不着,又千里跋涉到这里。听说靳大人就要进京,想请携带我们到北京见见光地……我倒勉强支撑得来,两个孩子实是走不动了……”说着,泪水早簌簌落下。
“难道安溪李家没人?”靳辅诧异地问道。
“有的……”秀芝抽咽着,已是泪湿襟袖,只矜持着没有放声,“他们……他们不肯认亲……”
靳辅和封志仁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,李光地家乃福建名族,怎么会这样没道理?靳辅嗫嚅了一下,终于问道:“两位少公子今年几岁了,怎么会生在杭州?”
“大人,这话不问也罢。”秀芝拭泪说道,“您如果疑我冒认官亲,就请治罪;如果信我就带我去;如果不肯带,也就罢了。欠您这杯水之情,来日叫光地还你就是。”说着便要起身。
这少妇柔声温言,淡淡几句话,倒把靳辅顶得一愣,忙道:“请不要误会,并没有疑你的意思,你如真的冒认官亲,怎敢和我同去见晋卿?”封志仁早叫过人来,吩咐收拾房屋,安排茶饭,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。
“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。”待秀芝他们出去,靳辅长吁了一口气,对封志仁笑道,“福建李家既不认她,李安溪认不认,还在两可之间。这里边怕有隐情呢!”
封志仁用扇子敲着手背,沉吟道:“这件事早就洞若观火了,只是她还回护着李大人,不肯说。李大人居丧丁忧期间,居然与青楼女子有私情,这‘道学’二字……唉!”靳辅一呆,蓦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,说道:“其实居丧不谨之罪还在其次,抛弃骨肉,为父不慈,更属丑闻。李光地如今炙手可热,等着进上书房,岂肯认这两大罪名?”说着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封志仁突然一笑,说道:“东翁太多虑了,我倒以为这是奇货可居。你若在北京替李大人悄悄掩饰过去,这个人情怕要比一万银子还值钱。东翁,李晋卿可是索额图中堂最得意的高足啊!”
隔了一日,靳辅便带了封志仁和秀芝母子三人起程了。因黄河淤沙早断了漕运水路,坐船眼见是不成的,便沿黄河北堤逆行向西,顺便沿途查看河情。过了开封向北折,进入直隶境内。靳辅等不进邯郸城,径自来到黄粱梦北的临洺关驿站落脚。
用罢晚饭,天已黑定了。靳辅穿一件绛红袍,也不套褂子,与封志仁一同踱出天井。遥见黄粱梦一带灯火辉煌,映得半边天光亮,便问:“志仁,你赶考多次从此路过,前头明晃晃的,是什么去处?”封志仁未及答话,驿站值夜的门吏在旁笑道:“抚台大人,您要明儿就走,小的劝爷去瞧瞧。那份热闹天下少有!明儿四月四,黄粱梦赛神,光戏台子就搭起六座。”靳辅笑着点点头,对封志仁道:“陪我走走,权作消食罢!”
二人边聊边走,半顿饭光景就到了黄粱梦,果真热闹非凡。庙里庙外上千支火烛,几百缸海灯燃着鸡蛋粗的灯捻,照得四周通明。一队队高跷有扮八仙的,有扮观音、孙悟空、猪八戒的,也有演唱西厢、牡丹亭之类故事的。六台大戏,东西两厢各三台,对着唱,锣鼓点子打得急雨敲棚一般。爆仗、起火炮乒乓乱响,根本听不清台上唱的是什么。戏台子下头人群拥来推去。什么卖瓜子儿的,卖麻糖、酥油茶的,卖酒食小吃的,一摊摊,一簇簇,应有尽有,摆卦卜爻、测字算命的先生亮着嗓门,可着劲儿高声喊叫……封志仁不无感慨地说道:“东翁,看来孔夫子难和太上老君、如来佛比呀!曲阜祭孔我也见过,哪里有这样的排场,这样的热闹!”
“战争未毕,太平盛境已经显露出来了。”靳辅的心情畅快了些,“只要不打仗,兴复快得很!志仁,你瞧见没有?这里还有洋货店,那么大的自鸣钟都摆上柜台了——魏东亭真是个有办法的人!”“那是,”封志仁笑道,“从海关运出去的是绸缎、茶叶、瓷器,我亲眼见过;返回的船上堆的那银子,海啦!”说着,二人便踅进后庙,在神道碑廊中就着烛光沿壁细看前人题词。有颂扬神道的,也有祈福求子的,还有抒发志向、牢骚的。靳辅因见到高士奇的批语,“狗放屁”三字颠来倒去地使用,哈哈大笑道:“这个姓高的真乃轻狂自大!”
“钱塘有名的才子嘛,心高眼空也是难免的。”封志仁一笑说道,“听说他批评别人文章、诗词,大抵只这三个字。‘放狗屁’属人放狗屁,偶一为之;‘狗放屁’是责其品行不端,文尚可取;‘放屁狗’是指专门放屁之狗责其人品文品俱劣……”他没说完,靳辅已是忍俊不禁,笑道:“总之都是放屁,优劣却在微妙之中——哦,这个陈潢的诗倒有趣:‘要与先生借枕头’。字也颇有风致——陈潢,这个名字好熟,再也想不起是何许人了!”
封志仁摇着扇子沉吟半晌,说道:“陈潢——陈天一嘛!钱塘陈守中的弟弟。因八字缺水,从小家中不禁他玩水弄潮,竟成了材!中丞想必忘了,你读过他的《扬水编》,不是击节称赏来着?”靳辅叹道:“原来是他!可惜,遭际不幸,竟流落至此!羡古人一梦风流,真令人惋惜——只恨不得一见!”
“不才在此,”身后忽然有人说道,“二位先生有何见教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