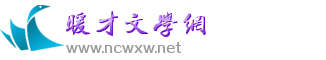大金牙拿起那座笔架左看右看,朝地上砸去。
萧暮雪一头撞了过去:“别动我爸爸的东西!”她这一撞拼尽了全力,撞得大金牙倒退了几步,撞得他怒从心起。他把钉耙往地上一扔,揪着萧暮雪的衣领将她拎起:“我表姐说得没错,你就是个讨人嫌的疯丫头。”
萧暮雪张嘴就咬,直到嘴里有了腥味也不松口。
大金牙松了手,抱着胳膊嗷嗷直叫:“你敢咬我?我踹死你!”他提脚朝萧暮雪踹去,萧暮雪躲闪不及,正中腰腹之间,疼得眼泪直流。
“别打她!”萧兰枢将萧暮雪护到身后,吼道,“她还是个孩子!跟大人的恩怨无关!”
“滚开!”大金牙取下墙上的笛子敲敲打打:“看不出来,你这教书先生除了会搬弄是非,还会这种没用的玩意。”
笛子上挂着流苏,是萧兰枢的心爱之物。萧暮雪生怕它被敲坏了。
“把笛子还我!”萧兰枢铁青着脸说,“这屋子里的东西,你想砸什么都随便你。唯独这把笛子,不是你这种人可以碰的。”
“哟呵,看来这笛子对你很重要啊!”大金牙满脸皆是得意之色,“既然它这么重要,那就更要砸了。”
萧兰枢抓住笛子,使劲拽。
大金牙使上扛包的蛮劲将他推开:“去你的!”
萧兰枢被推了个趔趄,站立不稳,整个身子朝后倒去。萧暮雪伸手去拉却没拉住,眼睁睁看他倒了下去,结结实实摔在地上。
“爸爸!”萧暮雪忍着痛挪到萧兰枢身边,“爸,您要不要紧?我扶您起来。”
萧兰枢直挺挺地躺着,双眼圆睁,瞪着屋顶。
萧暮雪心脏狂跳:“爸……爸?爸……!”
血,从萧兰枢的头下流出来,那把尖利无比的钉耙,钉穿了他的后脑勺!
大金牙傻了,傻站了很久才回过神来。他冲出书房,招呼闹事者一哄而散。
院子里又重新安静下来。死亡的脚步总是这样悄无声息,不约而至。
血汩汩地往外冒。很快,萧兰枢就躺在鲜血中了。萧暮雪跪在他身边,看着越积越多的血,已经忘记了该怎么流泪怎么悲伤怎么救治。
“雪……雪儿……”萧兰枢费力地将笛子举起,“好好收……收着……”
“爸,您别说话……别说话!”萧暮雪脱下衬衫,把它堵在流血的地方,“您会没事的!有我在,您……您会没事的……会没事的……”
萧兰枢笑容惨淡,双目开合间已没了精气神:“答……答应爸爸……永远不……不要放弃学业!”
“我答应!我答应!我什么都答应!爸爸,求求您不要有事!”萧暮雪的眼泪流得比血还多:“我求求您!您千万不要有事,我和妈妈不能没有您!我……我还没上大学,我还没实现梦想……您……您不能丢下我!”
“爸爸也……也舍不得你们……”
“我这就去给您拿药!爷爷留了药,我……我这就去拿!”
“傻孩子……不……不用了……”萧兰枢抬起沾满血的手,擦去萧暮雪滚烫的眼泪,“爸爸……爸爸爱……爱……爱你……!”话音未落,那只舞文弄墨,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手,颓然坠落!
萧暮雪凄声哀嚎:“爸!爸……”
太阳躲进云层,云层变得厚重起来。树影憧憧,风声渐起。相思鸟在笼子里胡乱扑腾,想给自己被囚禁的愤怒寻找出口。
萧暮雪手握长笛,面如霜雪,不声不响地跪在萧兰枢身旁,像一座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知觉的石雕。若不是有眼泪不停从她眼里涌出来,很容易让人误会她是个死人。她看着萧兰枢睁着的眼和他眼角的那汪眼泪,内心千疮百孔。她就那么跪着,跪着,跪着……一直跪到傅雪峰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。她看看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的苏婉言,再看看双目含泪的傅雪峰,依旧安安静静地跪着。
傅雪峰拼命克制对血的狂躁,双手快攥出血来:是谁这样残忍?是谁下的狠手?是谁在这样伤害她?我一定会找到他,叫他血债血偿!他看着脸色青白的萧暮雪,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
萧暮雪合上萧兰枢的眼,又对着他满是血的脸哀默良久,才扶着桌子起身。许是跪得太久了,双腿麻木得像木棍,根本无法走路。她直挺挺地站着,站着……直到能动了,才像个木偶一样摇摇晃晃地出了书房门。
屋外阳光毒辣,白晃晃地晃得人睁不开眼,空气中弥散着浓郁的血腥味。蜜蜂和蝴蝶围着新开的花嘤嘤嗡嗡争先恐后地说着情话,困倦的鸟儿藏身在树叶下,做着美梦打着盹,好不惬意。
天是血红的,地是血红的,竹林是血红的,树木是血红的,就连那姹紫嫣红的花朵,也都是血红的颜色。最不可思议的,是萧暮雪看见自己的头发也是血红色的。整个世界在她眼里,就是血的汪洋大海!她好像听见有人在叫自己,又好像听见有人在说话,却始终听不清说话的内容。她睁大眼寻找,什么也没找到。目光过处,只有一片血红——一片虚无又刺眼的血红!我在哪里?我在做什么?她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,忽而又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潮水般的席卷而来。好冷!怎么这么冷!她瑟缩着张望,想要找个温暖的地方,一不留神,萧兰枢淡金的脸庞入了眼。她怔住,猛然间心头一阵翻滚,一种滚烫的东西顺着喉咙喷涌而出。“哇”的一声,一口血吐了出来,吐了傅雪峰一身。紧接着,又是一口,再一口……像是呕吐般,她吐干净了堵在心头的恐惧,身体变得轻盈起来。她指着挂在天空的太阳,露出一抹奇怪而扭曲的笑:“太阳,落了!”说完,颓然向地上倒去。
傅雪峰身子一动,将她抱在了怀里。
整整两天,萧暮雪都在梦里挣扎。周围火光熊熊,她置身其中,却找不到出口。她拼命呼喊,拼命奔跑,拼命求救,却始终看不见人,得不到回应。火烧着了她的身体,她并没有感受到疼痛,只闻见皮肉的恶臭和骨头炸裂的声音。红色的液体从远处淌过来,渐渐漫过了她的脚面,她的腰身,她的胸口……直到没过她的头顶。那液体由温热变得滚烫,带着丝丝缕缕的血腥气。好熟悉的气味!似乎在哪里闻过。啊,对了,我想起来了,这是爸爸的血!爸爸的血?爸爸?爸爸……爸爸死了!不会的!他不会死的!我们说好了要一起读遍中外名著,一起游遍名山大川,一起陪着妈妈看夕阳,一起享受生命的每一天。他不会失信于我的,他不会!
雪儿……雪儿……雪儿……
是谁在叫我?是谁?萧暮雪循声望去,费了很大劲才看见烟火里影影绰绰的两个人影。谁?是谁在那里?
是我,雪儿。我是爷爷。
还有我,爸爸。
烟雾散去,露出两张带笑的脸来。
啊,爷爷,爸爸,我终于找到你们了!
傻孩子,我们一直都在你身边啊!
我找不到你们了,我好害怕!
别怕,我们都陪着你呢!回去吧,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
萧暮雪想抓住那两只手,却怎么也抓不住。
烟雾骤起,苏世安和萧兰枢的身影重新没入浓烟中。
火更大了,血更烫了,萧暮雪的心碎了!她对着黑色的天空疯狂吼叫,直至声嘶力竭。眼泪涌出来,俨然是红色的。嗓子眼堵得难受,一张嘴,吐出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来。仔细辨认,原来是自己的心肺。她看着还在跳动的心肺,愤恨地笑了:若不是你太弱小,怎么会家破人亡?为什么?为什么不保护好重要的人?为什么?为什么??为什么???她疯狂地踩踏那团心肺,直到它们爆裂成一摊肉泥。她若无其事地擦干净溅在身上的自己的血肉,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,转身扑进了冲天的火光中。
身后传来叶寒川撕裂的叫声。萧暮雪怨毒的眼里掠过仅存的一点温柔,她低头看看就要化成灰烬的身体,流下了最后一滴眼泪……
傅雪峰守着了无生气的萧暮雪,第一次知道担惊受怕的滋味。在明枪暗箭中求活时,他没害怕;被人满世界追杀时,他没害怕;被兄弟出卖命悬一线时,他没害怕;一夜之间从天堂到地狱,他也没害怕。但看过那日的萧暮雪后,他知道了什么是害怕:他害怕她受不住打击,他害怕她眼里的绝望,他害怕她诡异冷绝的笑,他害怕她惨白嘴角的血色,他害怕她生无可恋的心碎……他害怕会因此而失去她!他不敢想这个问题,不敢想失去萧暮雪的自己会怎样。是沉沦哀伤?是嗜血疯狂?还是大开杀戒?他撇开那些可怕的想法,死守内心的清明。好在苏婉言要忙葬礼,将萧暮雪全权托付给他,他没有太多时间去想以后的事情,只一心一意照顾昏睡的人。
葬礼当天,萧暮雪醒来,全然不知自己是死是活。棉花糖温暖的鼻息喷在她脸上,她才恍然想起自己还在人间。
有鼓乐声入耳。这是要开追悼会么?目光落在枕边那套黑色的丧服上,她双目轻颤,却没有流泪,只默默地穿戴整齐。下了床,头重脚轻的眩晕差点将她击倒,她扶墙而立,站了站才算好。
傅雪峰推门进来,惊喜极了:“没事了?”
萧暮雪看了他片刻,指着他身上的衣服问:“你要为爸爸披麻戴孝?是你自愿的,还是妈妈请求的?”
“是爸爸,我愿意。”
萧暮雪含泪笑了。
时代是新的,但山村的婚丧嫁娶依旧遵循祖宗规矩。死者若没有男丁披麻戴孝,便不能葬入祖坟,不能受子孙后代祭拜,不能入族谱,不能上天堂,只能算是游魂。所以,没有男孩子的家庭,要么招婿入赘,要么认有干亲。
院子里挤满了人,有很多萧暮雪都不认识,那是萧兰枢生前资助过的学生和贫困家庭。他们中有的不远千里而来,只为向他鞠一躬,说声谢谢。
萧暮雪一眼便瞧见了停在桂花树下的棺椁,眼前一黑,身子晃了几晃。
傅雪峰忙伸手相扶:“别怕。”
萧暮雪稳住心绪,摘了一朵早开的白菊插在鬓边。
苏婉言摸了摸她瘦削的脸颊,哀哀哭了。
萧暮雪沉声道:“妈,别哭了!爸爸最不喜欢看见亲人为他流泪,别让他走的不安心。走吧,咱们一起送爸爸最后一程。”
七婶说:“是啊,要赶在太阳出来前让死者入土为安,他才能再世为人。你们动作都麻利点,别错过了好时辰!”
“还得再等等,雪峰还没拜见族中长辈。”苏婉言带着傅雪峰进了堂屋,那里早已设好了香案。“族长,各位前辈,我苏婉言以萧家全家之名,请求各位为这孩子正名。”
傅雪峰懂事地在香案前跪下,拜见了肃穆端坐的长者,等着听训。
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举着萧氏宗亲的牌位问:“傅雪峰,你可是自愿认亲?”
“是!”
“你可愿与萧家风雨共担,敬老爱幼,有始有终?”
“愿意!”
“你可会恪守祖训,遵萧家家规,持身守正,与人为善,戒骄奢之态,行光明磊落事,做顶天立地人?”
“会!”
“是个有义气的好儿郎!今天,我谨以族长之名,代表萧姓族人,承认你异姓养子的身份。从今往后,萧家便是你的家。百年之后,你的名字会和萧家子孙一起列入萧氏族谱,享后人祭拜。叩头,行礼!”
傅雪峰恭恭敬敬地磕完三个头,将一碗酒举过头顶,无比谦恭地递到苏婉言面前,又无比虔诚地叫了声“妈”。苏婉言接过碗,一饮而尽。萧暮雪站到傅雪峰对面,双腿微屈,认认真真地行了礼,叫了声“哥哥”。
“礼成!”
苏婉言抹着泪说:“这认子之礼这样简单,免去了诸多环节,我知道是您老成全。谢谢您!”
“我帮不上你的忙,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细枝末节了。逝者已逝,活着的人要努力朝前看。你还有这么听话懂事的儿女,想开点吧!”
苏婉言擦擦眼睛,点了点头。
萧暮雪说:“太爷爷,我们要去送爸爸了,等事情结束了再去答谢您。”
“去吧!替我给兰枢上炷香。哎……”
萧暮雪应下,搀着苏婉言出了堂屋。
棺椁已抬上了汉子们的肩膀。傅雪峰怀捧萧兰枢的照片走在队伍的前面,苏婉言和萧暮雪一左一右扶着木棺,缓缓跟随。叫魂的和哭灵的拖着悠长的哭腔,呼喊着亡者的名字,一步一叫,一叫一哭。这叫声和哭声真挚动人,哀哀欲绝,但哭的人和死的人却是毫不相干也素不相识的。倒是那些血脉交融的人,只静默地陪着那隔绝了生死的棺材,不哭不闹。
萧兰枢的坟和苏世安的坟相隔咫尺,只是位置比苏世安的略低了些,位于其左下方,同样的青石墓碑,同样的坐南朝北,同样的绿树环绕。
这坟地原本是一处地势较险没人要的荒地。背靠小山坡,面朝重重叠叠的群山翠岭,三面悬空,自成一体。苏世安在世时,经村上批准,以地换地,将其划在萧家名下。之后,萧兰枢请了壮劳力,花了几天功夫,将这荒地改造成一块四棱见方的水田,并在山坡上栽种了翠柏,树脚下洒满了野花的种子。田埂的左边种桃树,右边栽梨树,前面则任由茅草、黄荆、野刺条和藤蔓疯长,渐渐长成一道天然屏障。几年下来,这里一改当日的荒芜,尤其是到了春天,花团锦簇,蝶舞蜂飞,成了村里最美丽的地方之一。
只一眼,萧暮雪就看明白了:苏婉言给了萧兰枢苏家长子的尊崇。等她百年后,则可葬于右下方。三座坟呈“品”字排列,相互守望,相互陪伴。
苏世安的坟上已有半人长的青草。萧暮雪看看那些草,又看看地里绿油油的庄稼,冷笑:想不到爷爷口中的良田好地,最后成了萧家两代家主的丧葬场。她看着那个巨大的坑,眼睛疼得挪不开。
棺材放在地上,又慢慢挪进那大小正合适的黄土坑里。抬棺的汉子用眼神问主家:埋么?
苏婉言哭倒在朱漆木棺上,已快要昏厥。
萧暮雪张了张嘴,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吐出两个没有情绪的字来:“埋吧。”送葬的人惊异地看着她,看着这个至始至终没流过一滴眼泪的姑娘,不知道是该夸她坚强,还是该说她无情。
萧暮雪始终挺直脊背站着,不言不语,不哭不闹,不痛不悲。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,只觉得这姑娘透着一股子阴冷的气息。尤其是她那双清凌凌的眼,平静,淡然,却无端地令人生畏。
只一袋烟的功夫,一座新坟赫然眼前,一个生命彻底消失。
是谁说过,当悲伤来临时,不是单个来的,而是成群结队的?这分明就是骗人的!因为,我这心里的悲伤,并不是成群结队的,而是无边无际的肆意汪洋。爸,我低估了悲伤的力量,我以为可以自救,却反而加速沉沦。我已无能为力,只能让悲伤浸透我的每个细胞。爸,我是该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,还是挺身反抗这人世无涯的苦难?您告诉我,我该怎么做?
没有人回答。因为没有谁能听见来自天堂与地狱的对话。
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洒落在山村的角角落落,温柔得让人热泪盈眶。送葬的人渐渐散去,苏婉言在七婶的搀扶下也回去了。萧暮雪跪在萧兰枢的坟前,一捧一捧向坟上添土。
傅雪峰站在一旁,目光随着她的动作回来移动。
晨风温热,吹动萧暮雪一身缁衣,吹落了枝头的花瓣,吹起了地里的黄土,将这落红和沙尘扬在天地之间,遮住了盛夏的朗朗晴空。
风过后,阳光明艳。萧暮雪抔完最后一捧土,掸了掸身上的尘土,向回家的路走去。傅雪峰审视着她的脸,想要探究她的内心,却见那张月牙色的脸上,除了平静,只有淡然。
回头看看红花与绿树环绕的新旧两座坟,傅雪峰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。